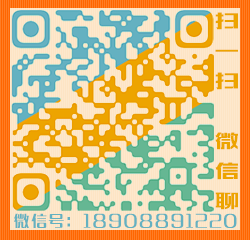德宏记行
在盆地里待久了,老是看到头顶上这块散不开的乌云,心中烦闷得很,我自从85年入川,至今十多年没见过一次盆地上空的中秋明月!有了机会总想出去透透气,所以刚一放假,我们就踏上了南行的路途。走出机舱来,昆明给人的第一个感觉是蓝天、丽日、白云、暖风,一句歌词跳出了心中:“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……”,真想放声高唱四川经典民歌:“太阳出来呦吼、喜洋洋喽喂……”,咳,不是盆地中人你还真难以体会这句民歌的真缔噢!让人不可思议的是,这个艳阳天下的南国大地在两天前还在飞舞着鹅毛大雪、使数万旅客滞留机场呢!昆明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,彩云之南名不虚传,这也是我三年之内两度踏上这块红土地的原因之一。至于另外的原因嘛,啊哈哈,我少年时期多次拜读赤脚作家艾芜的《南行记》和《南行记续篇》,对傣乡热带风情和那大青树下的小卜哨十分向往,曾立志要娶一个傣家小卜哨为妻。但那个年代理想只能是空想,等我有机会第一次来到版纳、进入傣乡时,已是不惑之年、“壮志难酬”了!但那彩云之南高大的大青树、婀娜的凤尾竹、俊俏的小卜哨仍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秀色虽不可“餐”,但可以赏,所以今天我要再次走进云南、走入傣乡。
边城除夕夜
飞机从昆明起飞,只需要四十多分钟就来到了傣乡的上空,最为引人的注目标志当然还是那婀娜多姿的凤尾竹了。从天空上看下去,芒市的农田很规范,整整齐齐的方块田,让人联想到那很可能是当年数十万支边青年的血汗作品,心情不由得格外激动。
芒市虽然是一州之首府,但毕竟是边城小镇,临近除夕夜的市面显得很清静,许多商店都在一片爆竹声中拉下了卷帘门。我们当然不管是不是除夕,抓紧时间看风景是唯一的目的。到过版纳的人都知道,在景宏的大街上如果你看到穿筒裙的女子,十有八九那是外来的游客赶时髦应景,而非真正的傣家卜哨。要看纯正的傣家姑娘,只有去橄榄坝。而芒市却不然,这里游客很少,满大街都是民族打扮的傣家女子,与版纳傣女的装束大同小异,细看略有区别:德宏傣寨按汉人称呼有“水傣”和“旱傣”之分,水傣一般指瑞丽、畹町等沿瑞丽江居住的“傣德”;旱傣则泛指潞西、梁河等其余地区的“傣勒”(版纳则是称“傣泐”)。水傣的装束是我们最为熟悉的彩色筒裙、齐胸短衣,头插鲜花。而旱傣的装束稍微朴素一些,特别是已婚妇女,一般都是黑色筒裙,黑色包头或白毛巾包头。与版纳傣族最为明显的是德宏傣族多穿大襟上衣,而版纳傣族多穿对襟上衣。由于德宏地区比版纳的气温略低,冬季的傣家女子还喜欢在民族上衣的外面罩上一件小西装,很象画了装等着上台就脱外套的女演员,让人看了别有一番风味。
游览过闻名全国的树包塔奇观和在《西游记》中多次出现的德宏军分区门口的大青树之后,天色已近黄昏,忽然想起可能要饿肚子!因为沿途到处都看到店铺在关门,许多赶街的傣家人已是急急匆匆地往回赶路。走了几条街,没看到一家卖吃的铺子,心中慌了神,赶快先买了几包方便面稳定军心,心想这个除夕夜的年饭很可能要和“康师傅”共度了。终于,在农贸市场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家还没来得及收摊的傣家小吃店,那是供赶街的傣族卖菜人填饱肚子那种“鸡毛小店”,几个傣族小青年正在边吃边喝酒,所以耽误了老板娘收摊,也因此使我们全家没在除夕夜来临之时饿一顿肚子。十三元钱的一顿年夜饭,吃了五个菜和一个汤,尽管身后杀鸡点的臭味不时飘过来,但还是吃的很高兴,总算不至于请康师傅和我们一同共进年饭了。
一寨两国风光
今天是年初一,早上喊车很困难,只好劳驾邮电宾馆的值班小姐传呼了一辆的士,平日里芒市到瑞丽只需100元的车费,今天非150元不干,只好任人宰割了。
芒市到瑞丽的公路还很不错,一百多公里路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。这都要归功于几年前的边贸开发热,当时来这里炒房地产的、倒运木材的、走私汽车的、贩卖毒品的,五花八门的所谓“开发”,闹腾的整个南疆一派火热景象。如今是时过境迁,走私贩毒一卡紧,缅甸又不搞商品经济,我们的所谓边贸是剃头挑子一头热,其他的各种附加开发活动随之降温,瑞丽变的冷冷清清,连旅游者也不多见了,每天从昆明只有一到两班飞机飞芒市,与昆明飞版纳的每十分钟一班飞机相比成为非常大的反差。
整个瑞丽三面被缅甸包围,拥有两个国家级口岸和一个省级口岸,与缅甸的木姐、南坎两市接壤,更多的地方是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,形成了一井两国、一寨两国、一房两国的国境线奇观。在瑞丽==弄岛的公路上,有一个叫芒修的傣寨,公路边上就是界碑,边防检查站就设在公路旁边,下了公共汽车走上十步就能出国。当然,我们这种持边境通行证的人是不能随便走出这十步的,而对于边民来说,根本不存在什么国境线,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寨子的乡亲嘛,甚至本来就是一座竹楼,哪里有什么边境线拦得住“这边”和“那边”?我纳闷的是这种公路沿着国境线修、检查站紧靠国境线建的景象只有在我们中国一方,而缅方则什么也没有,真正的国门大开,既无军人也没有检查站。这种现象在姐告口岸、畹町口岸和弄岛口岸都能看到,似乎边境只是中国一方的,只有中国武警和警察防守,根本不见缅方军警的影子。在姐告边境的缅方一侧甚至有中国边防武警的办事机构,让你看了大吃一惊:我的感觉是中国已经完全“镇住了”对方。94年时我到过中越边境友谊关附近的弄饶和波寨两个小口岸,也有同样感觉,让人怀疑边境冲突时究竟是谁先打谁的?
瑞丽街头的孟加拉流浪汉
在瑞丽的边贸商品街和姐告口岸一带,常可看到一些皮肤幽黑、身材矮小、眼睛很大、鼻子较直身穿花格筒裙的男人,他们是从缅甸过来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人。这些人整天在口岸附近流浪,有时帮助进仓库的货车卸卸货挣点钱,有时三五成群的站在街边什么也不做。他们没有固定的职业和住址,大部分是白天进来、晚上又回缅方,有些人也偷偷在瑞丽的贫民窟里住。从形象上看他们和印度电影《流浪者》里的拉兹差不多,只是“尺寸”要小一些。他们会在你逛边贸街时突然过来拍拍你的肩膀,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跟你打招呼:“好久没见你啊!”,让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,半天回不过神来。其实,他是与你拉近乎,希望你买他手上的玉镯或是小玉挂件,晚上逛边贸市场遇到几个这种人真让人有点心虚。国旅的老杨说,不用怕,这些人虽然卖的全是假货或者低档货,但是偷抢扒拿的事好象还没听说过,毕竟他们没有正式的中国护照和边境证件,犯了事可没有他的好果子吃。这种现象在其他地方从来没有听说过,也算是边城瑞丽的一景吧。
我看到了傣家小卜哨丢包!
年初三,我们的行程已满,该是返程的时候了。车子刚出瑞丽,就发现路边不时的有三五成群的傣家小卜哨,她们头戴成串的塑料花,身穿粉红色短上衣,由于下雨,外面还笼了件不扣扣的小西装,下身着彩色筒裙,打扮的真可谓是花枝招展,沿着公路边走边说笑着什么。我想可能这是哪家姑娘出嫁,她们是我们内地人所说的伴娘吧?从畹町到遮放是平坝地段,公路两边这种打扮的小卜哨越来越多,而且还看到路的另外一边往往是一群傣家小伙子,我不禁怀疑起来,哪有这么多冒雨在公路边迎亲的年轻人呢?于是便注意着观察路边人群的举动,这时一辆车子从对面开过来,由于下雨路滑,车速不快,使我有幸看到了令人激动的一幕:在车子开过路两边姑娘和小伙的一瞬间,姑娘们“喔——喂!”的一声喊叫,隔着公路和汽车迅速抛出了一个个物体,小伙子们则跳起来接在手中。啊!是丢包!!原来舞台上大家看到的丢包习俗,实实在在的是现实生活的写照,不同的是舞台上反映的多是在凤尾竹林里,而现实却是在公路两边。咳,傣族青年太浪漫了,这真是诗歌一样的生活啊!老杨告诉我们,每年的春节期间是傣家少年谈情说爱的浪漫季节,傣族是完全的婚姻自主,恋爱自由,十五六岁以上的姑娘都会出去丢包,当然不是象舞台上那样丢一次包就订下终身,而是把丢包当成一种交际的形式,丢多了当然就是有意思了。至于为什么要隔着公路、隔着汽车丢?这大概是现代丢包的一种创造吧?我猜想那是为了防止丢的时候尴尬,丢过去万一对方不接招也不难为情吧?能在傣乡欣赏到这种原始的爱情游戏,真是不虚此行啊!
来源:德宏信息港